拍下70部禁片后,她成了学者

铃木凉美
年近40,凉美渐渐觉得,在这烂屋子下苟活只是自欺欺人,不如推倒了重建。

胸大无脑。
许多人第一次见到铃木凉美时,脑子里冒出来的大概就是这句。

这是对女性普遍的偏见,几乎是刻在潜意识里的,真是荒谬。
今年7月,第167届芥川文学奖入围名单公布,铃木凉美的处女作小说《资优》入围了。
芥川奖是日本最权威的纯文学奖,能入围足以说明其实力,但与其他四位入围的女作家相比,铃木凉美的争议性铺天盖地。

人们争论的不是她的作品本身如何,而是因为她那「上不了台面」的黑历史。
她做过陪酒女,当过女优,拍过70多部AV片...
但隐退之后,她摇身一变成为了记者、作家和社会学者,作品的成就有目共睹,绝不是噱头。
这样的反转很容易被大众脑补成「穷家女为谋生沦落风尘后,勇敢逆袭」或「女记者为求真相,深入险境」。
但铃木凉美的经历绝不如此俗套,苦难叙事从来都不在她的人生剧本中。
01
铃木凉美,天生赢家。
1983年,她出生在日本东京,家境十分优渥。
父亲铃木晶,是日本著名的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翻译的琼·史密斯的《厌女症》、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颇为经典。

母亲灰岛佳里,同样是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儿童文学研究者,家大业大,完全是贵族小姐。

家里的书房上上下下,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远非一般的小型书店能比。


凉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对这些生涩的学问并不拒绝,而是早早就开始了思想上的叛逆,敢于质疑传统价值。
高中时期,辣妹文化风靡日本,凉美恋上了这疯狂中带点虚无的感觉。

她极力模仿着安室奈美惠,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画着烟熏大浓妆,校服裙摆折得越短越好。

每天放学后,她就会跟几个辣妹朋友,混在卡拉ok厅里,酒吧里,一切声光电喧嚣的地方都会有她们的身影。
「幸福的人,在这里会很少质疑自己的幸福感;不安和缺失的人,可以在这里寻找,然后被填满。」
跟迷失在这里的人不同,凉美对这个世界既向往,又疏离,她说自己带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憧憬苦难和黑暗的心态」。
16岁那年,凉美常常逃课,去涩谷的「原味店」卖内衣,但她要做的却不是卖普普通通的内衣。

那家店的营销策略是:售卖内衣的女生全都站在单面镜后边,她们看不见男性顾客,但对方可以看见她们。
男顾客像挑选商品一样,挑选他们中意的女生,然后把她带到另一间装有单面镜的小房间里。
在「你看得到我,我却看不到你」的状态下,她们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递给客户,供对方自慰。
虽说隔着单面镜,但受光线角度的影响,她们其实可以隐约看到对方。
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了男性勃起时的模样,第一次看到男性套着她的内裤手淫,那一次她赚到了一万五千日元。
她以这种方式目睹了各种各样男人的性欲,那场面丑陋至极。
自那之后,她翻出了自己的旧内衣,故意蹭上粉底,喷上廉价的香水,拿这些东西轻松换钱。
在男人眼中,她们是赚着脏钱的廉价女人,而在她们眼中,他们不过是用自己辛苦得来的报酬,买着虚假的体味,射精后满足离开的蠢蛋。
「男人真是一无是处啊!」
直到今天,她对男女关系的理解都停留在16岁那年,什么爱情,什么性爱,都那么不值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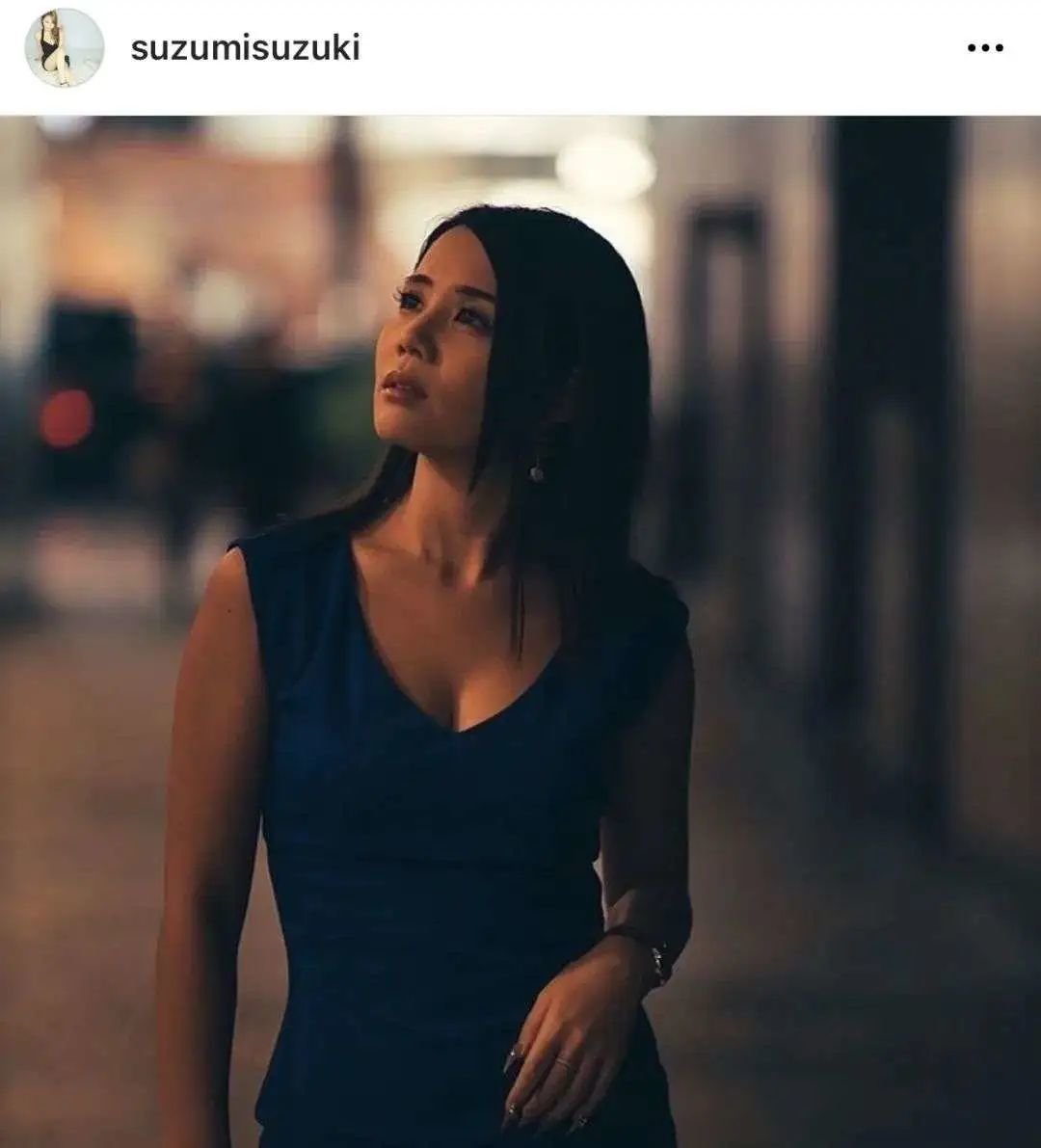
整个高一高二,凉美就这么荒唐地度过了,临近高三,她开始思考「当高中生的肉体不再值钱之后,自己还能做什么」。
某天她忽然对朋友们丢下一句:「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
然后她用一年的时间埋头于功课,考上了日本知名的庆应大学。
一切都像电影《垫底辣妹》那样,坏学生走向正轨,迎来了光明的未来。
但她的人生,却又再次脱轨。
02
与普通的大学生不同,凉美对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社会实践没有兴趣。
还有什么实践,比她曾看到的社会,更社会的呢?
于是她又走进了歌舞俱乐部,在那里当一名陪酒女郎。
每当入夜,男人们就会来这里买醉或买春,无论他们在白天时有多光鲜亮丽,夜晚他们拜倒在石榴裙下时,都大差不差。
人性的真实有时候很丑陋,但它似乎又有一种鬼魅的迷人。
「风俗业的氛围很迷离,就像掉进黑洞一样,容易让人越陷越深。」

她交了个男朋友,但这段关系或许只关寂寞,无关爱情。
男友是个AV女优星探,他劝凉美干脆去拍片,凉美答应了,不是为了金钱,只是为了反叛。
她讨厌父母的强大,厌恶他们的光环。
前面说过,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在母亲的眼中,凉美自然是她的研究对象之一。
母亲给了她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凉美却觉得:「母亲给予的自由夹杂着捕猎者的观察,像是一种真人互动实验,并饶有兴致地等待着实验结果。」
为了逃脱实验品般的命运,她狠下心用一种母亲完全预料不到的选择来回击。
也许这条路近乎自毁,但看到父母权威的崩溃,她觉得自己终于掰回了一局。

2004年,凉美以「佐藤琉璃」的艺名正式出道,参演的作品达到70部以上。
AV女演员的路并不好走,青春饭最多吃个四五年,出道时间越长,片酬越低,待遇越差。
若还想在这一行挣钱,就只能去拍一些别人不愿意接的类型,那种几乎全是凌辱类的,不把自己的自尊心扔进阴沟里,很难拍得出来。
拍片的危险性也很大,她曾被人用绳子吊在半空中,直至缺氧窒息,也曾有人不小心点着了喷在她背上的杀虫剂,留下一大片烧伤的疤痕。
身体的疼痛之外,凉美还面临着内心的撕裂。
虽然身处风俗行业,但她又不完全沦落其中,别的演员在片场聊天刷手机,她却捧着难啃的书籍在旁边安静阅读。
「一边擦拭射在身上的精液,一边读鲍德里亚」,这样的状态,凉美捱了4年。

她过气了,也厌倦了,回头看看那些经历,真是心酸。
交往过的男友一边对她说「我不在乎你的过去」,一边又在朋友面前坦言「谁会真的愿意和 AV女演员交往呢?」
跟男友性爱时,她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你AV都拍过了,肯定在吃药,就让我不戴套直接上吧。」
甚至有人会直接命令她:「照着这部片里的样子伺候我!」
而原本,她可以不经历这些的。
2008年,凉美正式退圈。
她把曾经烧伤的地方做了纹身,好让疤痕不那么触目惊心,但有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粉饰不了的。

03
在她最叛逆的高中时代,母亲对她说: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你可以走别人眼里的歪路,你可以去犯错,但当你离经叛道的时候,依然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人生这样才会平衡。」
尽管她对母亲的情感比较复杂,但这句话她是一直刻在心里的。

「从良」之后,她把这些年的见闻和感想悉数记录了下来,还如实披露了行业里的剥削和种种不堪。
这篇社会学论文,让她成功录取了东京大学的硕士生。
而随后出版的《AV女优社会学》,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此,她又成为了《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这是无数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体面工作。

她隐姓埋名,将书写对象对准了普通女性,关注她们的困境,替她们发声,文笔犀利大胆,很快成为了业界闪耀的新星。

但她并没有贪恋在这个行业里越来越高的地位,五年后她选择离职,成为了独立撰稿人。

就在过去的一切即将「洗白」时,《周刊文春》放出了《原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曾是成人片女演员》一文,她的过去被公之于众,铺天盖地的荡妇羞辱随之而来。

参加电视节目时,唯独她的着装有「特殊要求」;
媒体对她的宣传,永远都带着情色的噱头;
即使隐退了十多年,她对外的照片依然是当年的AV照...
凉美自嘲道:「露屁眼儿已经露习惯了。」
对于情色,她一向是鄙夷的,她把这当成自己的「情色资本」:
「管他三七二十一,趁老娘还年轻漂亮,把男人的钱卷走再说。如有必要,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
这不是媚男,而是厌男。

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女人的身体从来就不属于自己,而是男权社会下用来规训女人的一把尺,并且冠之以「道德」之名,而这份「道德」却并不用来衡量男人。
若一把钥匙能开很多把锁,它就被称为万能钥匙,而若一把锁能被很多个钥匙打开,就只能说明这是把烂锁。
男人是钥匙,女人是锁,身份不能互换,只有少数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只有极个别人会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叛。
凉美属于后者,代价极大。甚至于说,她输了,只是输得起而已。

成为作家多年,凉美从女优变成了为女性书写的战士。
曾经的她,早早就对社会和男性不抱任何希望,世界就是个烂屋子,想办法找个角落舒舒服服地活下去吧!
但年近40,凉美渐渐觉得,在这烂屋子下苟活只是自欺欺人,不如推倒了重建。
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只能敲个小窟窿,但一个能照进光的世界,总比一片漆黑强得多。
「您希望留给妹妹们一个怎样的世界?」
凉美回答:「我还是希望,妹妹们能活在一个不会被人搞得心烦意闷、辗转反侧的世界里,每年能比我少熬那样一个夜晚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