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的类型化与文学性真的是二元对立关系吗?
各位《四味毒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强,我是一名编剧,同时也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今天非常高兴能借助《四味毒叔》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对时下一些内容和故事创作上的思考和看法。很长时间以来,大家觉得类型和文学是有清晰的对立关系的,这两者有非常清楚的不同,最简单最表象的来讲,大家都能想到类型化的故事好看、非常吸引人、欲罢不能、情节紧凑,但是看完之后会觉得好像缺少一些更深的刺激,更清晰的一些体验,缺少更深的思考,它好像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营养。
而文学性很强的故事恰恰相反,它可能读起来不那么精彩、好看,或者说用我们的某种语言讲,它的门槛有点高,让你对它有点望而生畏。但是观赏它、阅读它、欣赏它之后往往会觉得有所获益,能从中间得到某些启发、某种力量、某些共鸣,这些东西它又被甚至是有些晦涩的表达方式所阻断着。眼下来讲这两者在逐渐地融合,在影视行业可能这些年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小说、在文学上可能已经很多年了,在影视上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今天想在这个主题下跟大家聊一些我个人的思考和判断。

首先类型化故事的主角是清晰的,观众和读者要代入谁、由谁引发、由谁代入、由谁构建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主角一上来就有很强的目的性。比如侦探小说,上来出现一个凶杀案,侦探要去破案,或者说有些犯罪小说,一个人犯罪了,杀了人了,他要怎么潜逃?上来就是很强烈的代入,而且完全符合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三幕剧结构,起承转合,剧作法,如何在一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在中间的时候经历一个虚假的胜利,在三分之二的时候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挫折和失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在最后去回应最开始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类型片、节拍表、三部剧类型,基本上类型化的故事是在这里面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题材上我们看到有各种创新,比如像奈飞现在很流行一些有很强烈的奇幻元素的作品,像《怪奇物语》《午夜弥撒》,它的反应是完全为读者或者观影者服务的,让你舒适、让你愉悦、让你能快速地代入这个故事,调动自己的多巴胺,产生很愉快的感受。类型化在这里面技术越来越完善,讲一个标准、扎实的故事,在各个平台都是变得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那文学呢?文学其实就得漫谈一些了,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标准来聊。文学其实是一直在跟哲学有很强烈的互动的,从尼采说上帝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上帝死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意向表达,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笃信的这些东西在不断地瓦解,比如我们相信人是上帝造的,我们相信人有血脉,皇帝他为什么比我高贵,因为他的血脉高贵,那现在我们血抽出来一化验都一样,这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去昧的时代。但是去昧的时代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是质疑,一个是迷茫。上帝死了,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了,那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今天会看到现在主要的、很多的文学在解答这个问题,我该如何成为我,我该怎么选择。我们现在讲所谓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就是以人的感受为核心去探讨一个故事,把原来巨大的宏大叙事、英雄叙事解构掉,让这些英雄和巨大的事件还原成人。
比如从最简单的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战争电影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它主角的官籍越拍越低。最早我们讲将军、讲领袖、讲元首、后面像《拯救大兵瑞恩》,你会看到他讲一个下级军官,《美国队长》讲一个连长、上尉,越来越用人的视角去讲宏大的叙事,不再讲珍珠港上层是怎么决策的,诺曼底登陆战略上是怎么博弈的,反而来讲一个小队,他们在这样巨大的历史事件下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人本,你要讲人的感受。当然这个说法很粗糙,但在人的感受中你会发现这些人变得有选择,他不再说有一个命令、有一个天职就无选择,他是最后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人都有的选,他并不是天生被塑造成这个人的,而是他选择成为这个人,我们讲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在这样的选择中,我们其实是把原来的这个没有去昧之前的世界加诸于人的一些天性拆解掉,比如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现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都对这点有所解构,来展现人细腻的复杂的情绪。或迷茫或失落,然后在这里面永远存在一个质疑,当我们迷信、笃信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质疑的,神塑造了人,人有罪,然后赎罪上天堂,你是没有自我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上去有的选了,上帝死掉了,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了,看上去有一种彻底的自由,但在这种彻底的自由之后,你又陷入了一种虚无和无助,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就是对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塑造自己,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权利变成了一种责任,变成了一种追问,甚至是一种拷问,他逼迫你必须回答,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我这样说比较简单,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现代思想史的一些书籍。所以你会看到这两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化的出发点是向外的,它要把这个故事做得非常好看、非常好卖、非常让人易于接受,而文学的出发点是向内的,它必须去讨论,去拷问人内在的情绪、情感和价值,一内一外。
而这两个东西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影视作品里有一个相对来讲泾渭分明的圈子,我们所谓的商业片、类型片、文艺电影、艺术片,包括现在国外有些艺术院线,它都不在一个地方上映。但这些年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类型片想要寻求更多的突破和价值,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它必然就会向文学化的东西里索取营养。长久以来很多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在寻求类型化的、有更广泛基础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漫谈的,这两者的交流,举几个例子,比如马特·达蒙演的《谍影重重》,讲一个间谍忘了自己是谁的过程中,如何跟一个女士结识,如何面对过往的事情,那些人来追杀他,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要寻找自己的记忆,然后与这些人对抗。它是一部非常清晰的商业类型片,但是自我的认知,你的身份是谁,你对自我的认知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中你是如何确立自我的,这样一个主题又是非常文学性的。法国有一个作家叫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写的非常有名的代表作《暗店街》,你乍一翻看上去就像一部非常类型的侦探推理小说,讲一个侦探忘了自己是谁,他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身份,但它本质上是更文学性的表达,它讲的是人对自己的身份,这个世界对一个人的身份,他该如何定义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学主题。你会看到马特·达蒙的《碟影重重》和《暗店街》表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只不过一个用了非常清楚的动作、间谍的类型化叙事,一个套了侦探小说的外包装,但底层是一个非常文学性的表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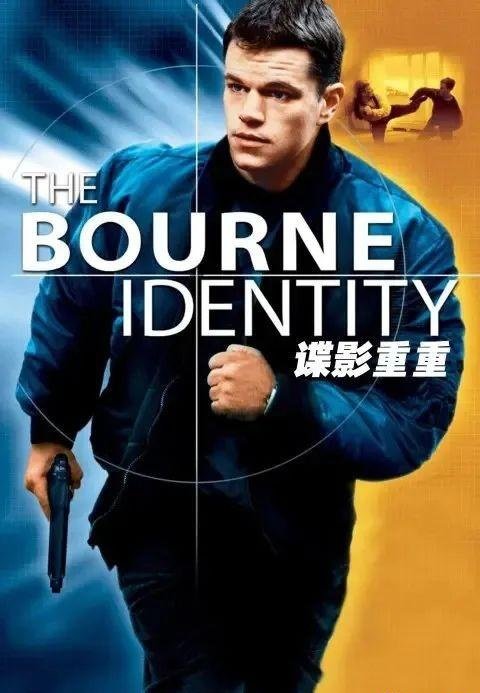
我们再来说近的,刚才我们提到有部片子叫《午夜弥撒》,它整个的讲述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小岛上的老牧师被变成了吸血鬼,然后他回到这个小镇完全变年轻了,小岛上的人都认不出来了,然后他用自己的血液给大家治病,看上去像是上帝的神迹在浮现一样,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忽然站起来了,老年痴呆的人忽然想起来了、能说话了,最后这个小镇的人慢慢的变得堕落,变成吸血鬼,在阳光初升下很多人焚烧成灰烬。它是一个非常哥特式的恐怖小说的东西,而只不过是它在表达的过程中加入了非常现代性和文学化的元素,我们在不断地反思我是谁的过程中,故事的主角,从小镇走出去,到了大城市,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遭受挫折又回到这个小地方,他在不断地确定自己是谁,然后在确定自我是谁的过程中跟宗教发生了如此深刻的联系,最后在质疑和反叛中去确立自己的价值,这本身是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主题,但它的表述又非常类型化,所以这个片子喜欢的人很喜欢,觉得很深刻,那不喜欢的人呢,又会觉得它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对奈飞故事打发时间的期待,它中间有些东西非常的缓慢、晦涩,大量的生活现状细节的描写,这就是《午夜弥撒》的这样一种融合。

在商业上更成功的,比如《鱿鱼游戏》,同时间前后还上映了《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其实跟《鱿鱼游戏》很像,也是死亡游戏型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虽然口碑也很好,但它在泛亚洲,甚至在全球的影响都不如《鱿鱼游戏》。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跟《弥留之国的爱丽丝》跟文学性结合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介绍,它虽然上来也做了很多日本所谓的otaku,御宅族的社会现状,但它做得比较淡,很快就进入了逃杀情景。而《鱿鱼游戏》在一开始用了非常坚实的篇幅去讲主角作为一个边缘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它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共鸣,很多同行说这种类型的东西是老梗,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很早就有,但这些东西又焕发了非常具有当下意义的生命力。比如《赌博默示录》,一个日本的漫画,后来也改编成中文电影,我们中国也翻拍过来,很棒的一个故事,里面有大量的死亡游戏、生死博弈的东西,但《鱿鱼游戏》把这些情境跟人的感受做了更深刻的关联,把里面边缘人的特质做了更大的放大,有更强的社会意义,所以它就产生了更强烈的冲击力和基础。

由此就扩展到像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电影是这个世界上最类型的类型故事了。我们看到DC、漫威宇宙这些,它们是最类型化的故事,但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很棒的超级英雄,比如《小丑》《新蝙蝠侠》,它越来越往人物内心的感受去出发,也变得有更强烈的文学性,也焕发了更大的生机。总体来讲,类型故事因为是类型化的,所以它的故事方式其实有很强烈的同质感。我们经常说现在的故事可能十几世纪就写完了,像狄更斯那一代人,他们所讲的这些故事类型化的这些东西其实在近一两百年内被大量的借鉴学习、重复。所以你单纯地从个人角度,单纯地说类型创新很艰难,这个世界上留给我们新的类型可能不多了,甚至没有了,你很难找到一个全新的故事讲述方式来跟大家交流,获得更多的认同,获得更多的关注。但类型创新的一个巨大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挖掘类型人物中的文学价值。因为故事的主题一定是通过故事的主角人物来承载的,不然它就变成论文了,没有故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观点输出,而故事还是需要通过人物去承载和呈现主题。
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一个去昧的世界,有一个词叫达尔文酸,就是进化论像酸一样,去腐蚀掉了原有世界的一切我们认为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神权的这些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达尔文酸腐蚀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讲到的人本的、存在的、解构的,我们去解构原有的这些诸神的世界,我们把它解构掉,我们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重视人的感受。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能让类型故事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和动力。我们通过更文学的手段去剖析人物、解构人物、去构建人物,让我们的类型化故事拥有跟当下的人更强烈共鸣的主题,让我们的故事拥有当下更强烈的生命力。我们常讲以人物为本,一流的故事应该做人物,这就是我从类型和文学的看似二元但其实是互相融合、相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谈论的我对眼下的类型故事的创新、文学故事的传播的看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这种趋势的理解,我认为它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它拥有一些强迫性,类型故事的文学性你无论怎么做都很难逃开,只是你是否有意识,是否把它做得好。比如说斯蒂芬·金,大家可能看到他的很多非常著名的恐怖故事,像《肖申克的救赎》就不说了,电影可能跟他的原作改动比较大,你会看到像《闪灵》《宠物公墓》,他的各种恐怖故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签,他讲述的恐怖的来源来自于美洲大地上印第安文明遗留下来这些东西,无论他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得类型化、讲得好看、讲得有趣有意思,他永远逃不脱一个主题,就是当现代文明去把印第安文明在那片土地上渐渐消磨之后,必然会面临这种原始的恐惧的反扑,这个东西你逃不开,它有强制性。

哪怕我们现在写一个再简单的故事,你会发现它仍旧跟今天人的自我认同很难彻底逃开关系。类型其实对文学性也产生了一些强制化,比如说我们看像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像刚才说到的《暗店街》。因为我们的类型故事讲了这么久,它的传播如此之深远,如此之迅速,如此之易于传播,导致大众对一个故事有了很清晰的期待,也许他不是编剧,不是作家,他不写故事,但因为这种东西被驯养的太多了,他看得太多了,所以一个故事如果不符合他的过往的审美的习惯,跟他的审美习惯有非常强烈的冲突,他也很难去真的代入。
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了,我们会看到近些年很多非常优秀的文学故事都在获得某种类型化,大家的阅读习惯、观影习惯也在强迫你。所以如何给类型故事赋予更强的文学性,让类型故事焕发出更强烈的生命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当然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做的是更商业的一些事情,所以纯粹的文学化的、艺术的东西,我能力有限,没法特别深刻地展开跟大家交流,我只能说大概是我现在对类型化的认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四味毒叔》,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或者是批评可以留言,我们都会很认真地去学习,非常感谢大家,再见